
從文字學角度看殷墟甲骨文的複雜性
裘錫圭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富达
我在《殷墟甲骨文在文字學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已經指出,在能夠反映當時文字面貌的可靠的古漢字資料中,殷墟甲骨文是時代最早的一種。同時還指出,甲骨文所代表的雖然是已經形成完整體系的漢字,但是由於其時代距離原始漢字最後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時間並不很遠🧜🏼♀️,還保留了一些在後來的古漢字中所看不到的比較原始的文字現象(上引文章見《古文字學論集·第一輯·甲骨學特輯》11-22頁🧜🏼♀️,漢城:東文選,1995。以下簡稱“重要性”)👨🏽🦰。
除了比較原始的一面🔳,殷墟甲骨文也有超前發展的一面。我們所能看到的商代文字資料👨🎓,主要是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殷墟甲骨文數量既多,內容也很豐富🩸,比商代金文更受重視🧙🏻。但是能夠代表商代文字的正體的卻是金文,甲骨文實際上是當時的一種俗體文字。在文字發展史上,俗體的發展往往有超前性,甲骨文正是如此🦴。
商代的金文通常是鑄在青銅器上的。鑄器前👩🏿💼,一般先用毛筆寫出字體規整的銘文,作爲製範鑄銘的底本🤘。在寫族名或其他帶有裝飾性的銘文時🧛🏿♀️🚯,還往往使用較古的很象形的字體,就像在隸書時代的人有時還用篆文銘刻金石一樣。殷墟甲骨文主要是甲骨卜辭,通常是直接用刀刻在占卜用的龜甲獸骨上的🌡。商代統治者每天都要進行很多次占卜,需要刻在甲骨上的卜辭數量很多🏋🏿♂️。刻字的人爲了提高效率,不得不改變毛筆字的字體🤏🏼,如改粗筆爲細筆🏆,改圓形爲方形等等🚱。此外還往往用其他辦法,如簡化字形、改變文字結構的種類(如改表意字爲形聲字)等,來使文字變得比較便於書寫。因此殷墟甲骨文一方面具有某些原始性👩❤️👨☆,另一方面作爲一種俗體文字🚣🏻,對同時代的甚至較晚的其他古漢字來說,無論在字體上或文字結構上🤳🥰,又都有一些超前的發展🪗。
關於殷墟甲骨文的原始性🛜,我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在甲骨卜辭中可以看到原始文字中用圖畫式手法表意的字形往往隨語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那種現象的殘跡。在本文開頭所引到的《重要性》中💱🧞♂️,我們曾舉過甲骨卜辭講到“![]() (登)鬯”的時候,有時把“
(登)鬯”的時候,有時把“![]() ”字所从的“豆”換成“鬯”的例子。在別的文章中還舉過其他例子(參看《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拙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262~26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並參看拙著《古文字論集》145頁,中華書局❣️,1992)🪸。在這裏我們再舉兩個跟“逐”字有關的例子🤵♀️。
”字所从的“豆”換成“鬯”的例子。在別的文章中還舉過其他例子(參看《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拙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262~26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並參看拙著《古文字論集》145頁,中華書局❣️,1992)🪸。在這裏我們再舉兩個跟“逐”字有關的例子🤵♀️。
《甲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32832有下引卜辭🤷🏽:
辛未貞:王其![]() (錄入者按:原字形為
(錄入者按:原字形為![]() )于□(此字不可確釋,應爲地名)。
)于□(此字不可確釋,應爲地名)。
于壬![]() (錄入者按:原字形為
(錄入者按:原字形為![]() )🧸。
)🧸。
這兩條卜辭裏的“![]() ”字,前人不識,因此辭義也無法講通。如果認識到了甲骨文原始性的一面,並對照一下下引的這些卜辭,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字,前人不識,因此辭義也無法講通。如果認識到了甲骨文原始性的一面,並對照一下下引的這些卜辭,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癸未卜貞💁:翌戊子王往逐![]() (校錄者按🫲:原字形作
(校錄者按🫲:原字形作![]() )。 《合》10506,《合》557有與此同文的卜辭。
)。 《合》10506,《合》557有與此同文的卜辭。
癸未卜殼貞☦️:多子獲![]() (校錄者按🤷:原字形作
(校錄者按🤷:原字形作![]() )。 《合》10501正
)。 《合》10501正
戊子卜𡧍貞🧏🏿♀️:王[往]逐![]() (校錄者按🤸🏻♀️:原字形作
(校錄者按🤸🏻♀️:原字形作![]() )于沚,亡災。之日王往逐
)于沚,亡災。之日王往逐![]() (校錄者按:原字形作
(校錄者按:原字形作![]() )于沚🤙🏻,允亡災,獲
)于沚🤙🏻,允亡災,獲![]() (校錄者按🧕🏽🦠:原字形作
(校錄者按🧕🏽🦠:原字形作 )八。 《合》9572
)八。 《合》9572
第一條卜辭的“![]() ”跟其他條的“
”跟其他條的“![]() ”,顯然指同一種東西📺。它是商王田獵時所追逐的獵物。“
”,顯然指同一種東西📺。它是商王田獵時所追逐的獵物。“![]() ”應該是從“隹”“
”應該是從“隹”“![]() ”聲的字💆🏿,所以可以假借“
”聲的字💆🏿,所以可以假借“![]() ”字來表示它🧜🏻♂️。甲骨文“逐”字本作“
”字來表示它🧜🏻♂️。甲骨文“逐”字本作“![]() ”👨🏼🦱。“止”即“趾”的初文🙋🏼♂️,象人的腳。“止”向“豕”,表示有人在追逐野猪🟪。前面所引的那兩條卜辭裏的“
”👨🏼🦱。“止”即“趾”的初文🙋🏼♂️,象人的腳。“止”向“豕”,表示有人在追逐野猪🟪。前面所引的那兩條卜辭裏的“![]() ”,顯然應該理解爲“逐
”,顯然應該理解爲“逐![]() ”。這樣理解,那兩條卜辭就都可以講通了。
”。這樣理解,那兩條卜辭就都可以講通了。
由於所逐的是![]() ,就把“逐”字所从的“豕”改爲“
,就把“逐”字所从的“豕”改爲“![]() ”👳🏿♀️,並用它來表示“逐
”👳🏿♀️,並用它來表示“逐![]() ”。這跟我們在《重要性》裏講到過的⚪️、在納西原始文字裏只要把“吼”子所从的牛頭形改成馬頭形就可以用它來表示“馬吼”的現象,是十分相似的。應該指出,納西原始文字裏的牛頭和馬頭都是象形的;甲骨文裏用來代換“逐”字所从的象形字“豕”的“
”。這跟我們在《重要性》裏講到過的⚪️、在納西原始文字裏只要把“吼”子所从的牛頭形改成馬頭形就可以用它來表示“馬吼”的現象,是十分相似的。應該指出,納西原始文字裏的牛頭和馬頭都是象形的;甲骨文裏用來代換“逐”字所从的象形字“豕”的“![]() ”字,卻已經是一個形聲字了。在用圖畫式手法表意的字形裏,竟使用形聲字作爲偏旁,這當然是文字體系發展的一種反映👨👦👦。不過這一點並不足以改變以“
”字,卻已經是一個形聲字了。在用圖畫式手法表意的字形裏,竟使用形聲字作爲偏旁,這當然是文字體系發展的一種反映👨👦👦。不過這一點並不足以改變以“![]() ”來表示“逐
”來表示“逐![]() ”這一文字現象的原始性。在後來的古漢字裏是絕對看不到這類現象的🥛。
”這一文字現象的原始性。在後來的古漢字裏是絕對看不到這類現象的🥛。
殷墟甲骨文還有構造跟“![]() ”相類的“
”相類的“![]() ”字。卜辭或言“
”字。卜辭或言“![]() 鹿”(《合》10294🐬、10296),文例也跟“逐”字相類(卜辭中“逐鹿”之語屢見🤱🏼,參看《殷墟甲骨刻辭類纂》328~329頁,中華書局,1989)。前人多將“
鹿”(《合》10294🐬、10296),文例也跟“逐”字相類(卜辭中“逐鹿”之語屢見🤱🏼,參看《殷墟甲骨刻辭類纂》328~329頁,中華書局,1989)。前人多將“![]() ”看作“逐”字的異體(見《甲骨文編》“逐”字條69頁第二、三行,中華書局1️⃣,1965),應該是可信的。這個字原來也應該是可以用來表示“逐兔”的(“逐”原來也應該可以用來表示“逐豕”)。
”看作“逐”字的異體(見《甲骨文編》“逐”字條69頁第二、三行,中華書局1️⃣,1965),應該是可信的。這個字原來也應該是可以用來表示“逐兔”的(“逐”原來也應該可以用來表示“逐豕”)。
唐蘭釋“![]() ”爲“逸”🐃,李孝定從之(《甲骨文字集釋》3085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古漢字對从“止”和从“辵”(辶)往往不加區別,前面說過🧔🏿♀️,“逐”字原來就是从“止”的🧑🏼🎓。所以從古漢字字形變化的通例來看,唐先生釋“
”爲“逸”🐃,李孝定從之(《甲骨文字集釋》3085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古漢字對从“止”和从“辵”(辶)往往不加區別,前面說過🧔🏿♀️,“逐”字原來就是从“止”的🧑🏼🎓。所以從古漢字字形變化的通例來看,唐先生釋“![]() ”爲“逸”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實際上他卻錯了。這一方面是由於對文例不夠重視,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沒有很好認識到殷墟甲骨文原始性的一面🧘🏿♀️⛹️。
”爲“逸”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實際上他卻錯了。這一方面是由於對文例不夠重視,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沒有很好認識到殷墟甲骨文原始性的一面🧘🏿♀️⛹️。
甲骨文又有“![]() ”字(《合》10654)📀,亦作“
”字(《合》10654)📀,亦作“![]() ”(《合》8256,參看《甲骨文編》“逐”字條69頁第一行🚪,所引“明570”即《合》8256的摹本)。葉玉森認爲“
”(《合》8256,參看《甲骨文編》“逐”字條69頁第一行🚪,所引“明570”即《合》8256的摹本)。葉玉森認爲“![]() 即逐之異體”(《鐵雲藏龜拾遺》6頁第8片考釋。這一片其實並無“
即逐之異體”(《鐵雲藏龜拾遺》6頁第8片考釋。這一片其實並無“![]() ”字,只有“鹿”字,葉氏誤將它跟下方的“亡”字合在一起👸🏽🌺,錯認爲“
”字,只有“鹿”字,葉氏誤將它跟下方的“亡”字合在一起👸🏽🌺,錯認爲“![]() ”字)🧑。由於這個字只見於文義不明的殘辭,它究竟是不是“逐”的異體,還無法肯定。不過從“
”字)🧑。由於這個字只見於文義不明的殘辭,它究竟是不是“逐”的異體,還無法肯定。不過從“![]() ”🧗♂️、“
”🧗♂️、“![]() ”二字的情況來看,這兩個字是有可能被用來表示“逐”或“逐鹿”的。
”二字的情況來看,這兩個字是有可能被用來表示“逐”或“逐鹿”的。
“![]() ”字見於辭尾記“十月在
”字見於辭尾記“十月在![]() ”的一條殘辭🧖♂️。在同時期的卜辭中,還有幾條也在辭末記“十月在
”的一條殘辭🧖♂️。在同時期的卜辭中,還有幾條也在辭末記“十月在![]() ”(“
”(“![]() ”或作“
”或作“![]() ”🧩🧠,二者是同一地名的不同寫法🙏🏿。這些卜辭都收錄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238頁)🥲。這幾條大都也是殘辭⚜️,只有《合》10945“貞:弗其擒🦍。十月。在
”🧩🧠,二者是同一地名的不同寫法🙏🏿。這些卜辭都收錄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238頁)🥲。這幾條大都也是殘辭⚜️,只有《合》10945“貞:弗其擒🦍。十月。在![]() ”一條是完整的🏮。這一條顯然與田獵有關。有“
”一條是完整的🏮。這一條顯然與田獵有關。有“![]() ”字的殘辭所記的月名和地名跟這一條相同🔪,大概也與田獵有關,“
”字的殘辭所記的月名和地名跟這一條相同🔪,大概也與田獵有關,“![]() ”是“逐”字異體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是“逐”字異體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現在我們來看另一個也是跟“逐”字有關的、反映甲骨文原始性的例子⚂。
下面所臨摹的是《合》20715號卜骨(即《鐵雲藏龜》193.1、《戰后京津新獲甲骨》2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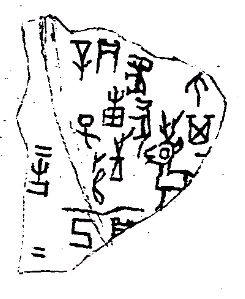
此片上的“辛巳”一辭,我認爲應該釋讀爲:
辛巳卜𠂤貞💥:甫往![]() (逐)鹿👨🏻🔧,不其
(逐)鹿👨🏻🔧,不其![]()
“甫”是人名🧑🏽🎨,卜辭中屢見👨🔬。“![]() ”字象犬逐兔,應該是“逐”的另一種異體。前人多將它們看作兩個字,辭義就講不通了✊🏿。這個字原來也應該是可以用來表示“犬逐兔”或“以犬逐兔”一類意思的。說不定刻這條卜辭的人,仍是爲了強調在所卜問的田獵活動中將要用犬逐鹿而選用這個字的。這條卜辭的“鹿”字也刻得特別象形,刻字者似乎有一種復古的傾向⌛️。
”字象犬逐兔,應該是“逐”的另一種異體。前人多將它們看作兩個字,辭義就講不通了✊🏿。這個字原來也應該是可以用來表示“犬逐兔”或“以犬逐兔”一類意思的。說不定刻這條卜辭的人,仍是爲了強調在所卜問的田獵活動中將要用犬逐鹿而選用這個字的。這條卜辭的“鹿”字也刻得特別象形,刻字者似乎有一種復古的傾向⌛️。
在原始文字裏,語音並不相近的兩個或幾個不同的詞,可以用同樣的字形作爲它們的表意字。例如在納西原始文字裏💩,象空氣流動的“![]() ”字,既代表“風”這個詞,又代表“春季”這個詞,因爲春天常常颳風,而這兩個詞的語音則相距甚遠(參看《方國瑜《納西象形文字譜》66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81)🚲。這類現象在古漢字中仍有殘存🤹🏻♂️,而以殷墟甲骨文最爲顯著🌈。例如在相當多的甲骨卜辭裏☕️。“月”和“夕”的字形並無區別🧝🏽♂️,“
”字,既代表“風”這個詞,又代表“春季”這個詞,因爲春天常常颳風,而這兩個詞的語音則相距甚遠(參看《方國瑜《納西象形文字譜》66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81)🚲。這類現象在古漢字中仍有殘存🤹🏻♂️,而以殷墟甲骨文最爲顯著🌈。例如在相當多的甲骨卜辭裏☕️。“月”和“夕”的字形並無區別🧝🏽♂️,“![]() ”也可以代表“夕”👩🏼💼,“
”也可以代表“夕”👩🏼💼,“![]() ”也可以代表“月”。在後來的古漢字裏,“月”和“夕”作爲表意偏旁有時可以通用👨🏿⚕️;作爲單字時不加區別的情況雖未絕跡,但已極爲少見➿🤹🏿♂️,跟殷墟甲骨卜辭的情況顯然有別🤹🏿。
”也可以代表“月”。在後來的古漢字裏,“月”和“夕”作爲表意偏旁有時可以通用👨🏿⚕️;作爲單字時不加區別的情況雖未絕跡,但已極爲少見➿🤹🏿♂️,跟殷墟甲骨卜辭的情況顯然有別🤹🏿。
殷墟甲骨文裏還有一些比較原始的文字現象,由於已經在我們的其他文章裏講過🍼,這裏就不重複了(參看上引《古代文史研究新探》263~264頁)。
下面我們再來看殷墟甲骨文超前發展的一面💇🏿♂️。
由於字體上改粗筆爲細筆🤷🏻♀️、改圓形爲方形等變化,在殷墟甲骨文裏出現了一些對古漢字來說顯得很特殊的字形👬🏻。例如“日”字,殷周金文多作![]()
![]() 等形(《金文編》455頁,中華書局🧍♂️,1985)🧍🏻,小篆“日”字的外框仍作豎橢圓形而不作方形,可是在殷墟甲骨文裏屬於早期的武丁時代的很多甲骨卜辭,卻已經把“日”字寫作“
等形(《金文編》455頁,中華書局🧍♂️,1985)🧍🏻,小篆“日”字的外框仍作豎橢圓形而不作方形,可是在殷墟甲骨文裏屬於早期的武丁時代的很多甲骨卜辭,卻已經把“日”字寫作“![]() ”了。這種跟隸書已經相當接近的寫法,並未爲晚於殷墟甲骨文的古漢字所繼承✬。隸書“日”字的寫法是來自篆文草體的。
”了。這種跟隸書已經相當接近的寫法,並未爲晚於殷墟甲骨文的古漢字所繼承✬。隸書“日”字的寫法是來自篆文草體的。
殷墟甲骨文裏簡化字很多,有不少簡化字似乎是爲它所獨有的☝🏻。例如子丑寅卯的“子”本作![]() ⚠️、
⚠️、![]() 等形,但是早在武丁時代的甲骨卜辭裏,就已經相當普遍地使用了它的簡化字形
等形,但是早在武丁時代的甲骨卜辭裏,就已經相當普遍地使用了它的簡化字形![]() 。這種字形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其他古漢字資料中還沒有出現過。晚期的甲骨卜辭一般也不用這種簡化字形,而仍用
。這種字形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其他古漢字資料中還沒有出現過。晚期的甲骨卜辭一般也不用這種簡化字形,而仍用![]() 一類字形。因此曾有甲骨學者認爲
一類字形。因此曾有甲骨學者認爲![]() 是由
是由![]() 演變而成的。這就把字形演變的過程弄顛倒了。又如“霍”字本作“雨”下三“隹”形,字形繁複😴📉,不便書寫。甲骨文裏對它有兩種簡化方法。一種是簡存輪廓的方法,即把它寫作
演變而成的。這就把字形演變的過程弄顛倒了。又如“霍”字本作“雨”下三“隹”形,字形繁複😴📉,不便書寫。甲骨文裏對它有兩種簡化方法。一種是簡存輪廓的方法,即把它寫作![]() 🥤,見于晚期卜辭。這也可以看作草體字,並非典型的簡化字🤽🏻。另一種是改變結構的方法🧑🧑🧒,即把它改爲从“雨”“隻”(古“獲”字)聲的形聲字📺,見於早期卜辭(參看《甲骨文編》186頁“霍”字條)👨🏻⚕️。這兩種簡化字形也都沒有爲後人所繼承💁🏽。後人所用的是減少“霍”字“隹”旁數量的方法。《說文》“霍”字篆形从二“隹”(周代金文已有从二“隹”的“霍”,參看《金文編》263頁),隸書、楷書一般只保留一個“隹”。
🥤,見于晚期卜辭。這也可以看作草體字,並非典型的簡化字🤽🏻。另一種是改變結構的方法🧑🧑🧒,即把它改爲从“雨”“隻”(古“獲”字)聲的形聲字📺,見於早期卜辭(參看《甲骨文編》186頁“霍”字條)👨🏻⚕️。這兩種簡化字形也都沒有爲後人所繼承💁🏽。後人所用的是減少“霍”字“隹”旁數量的方法。《說文》“霍”字篆形从二“隹”(周代金文已有从二“隹”的“霍”,參看《金文編》263頁),隸書、楷書一般只保留一個“隹”。
還應該指出,有些一般認爲出現得較晚的字形💳,在殷墟甲骨文裏其實就已經出現了。例如“涉”字,在古漢字裏通常把它所从的“止”和“![]() ”分寫在“水”的兩邊,不但甲骨文、金文如此🤶🏻,直到戰國時代楚國的簡帛文字仍然如此(參看高明《古文字類編》468頁“涉”字條,中華書局,1980)。一般認爲把“涉”字寫作从“水”从“步”是從小篆開始的。其實早在武丁時代的甲骨卜辭裏👨🦰,就已經出現了這種“涉”字🐚,例如《合》21256“
”分寫在“水”的兩邊,不但甲骨文、金文如此🤶🏻,直到戰國時代楚國的簡帛文字仍然如此(參看高明《古文字類編》468頁“涉”字條,中華書局,1980)。一般認爲把“涉”字寫作从“水”从“步”是從小篆開始的。其實早在武丁時代的甲骨卜辭裏👨🦰,就已經出現了這種“涉”字🐚,例如《合》21256“![]() 涉朿”一辭中的“涉”。這個“涉”字所从的趾形比一般武丁卜辭寫得更爲象形,但“水”旁已經省作“
涉朿”一辭中的“涉”。這個“涉”字所从的趾形比一般武丁卜辭寫得更爲象形,但“水”旁已經省作“![]() ”,“止”和“
”,“止”和“![]() ”寫在同一側🏃🏻♀️➡️,與一般“步”字無別(武丁卜辭中還有在“水”的兩邊都有“步”的“涉”字,趾形也寫得比較象形📁,見《合》20464.从“水”从“步”的“涉”可能是由它簡化而成的♜。《合》“1051正”有
”寫在同一側🏃🏻♀️➡️,與一般“步”字無別(武丁卜辭中還有在“水”的兩邊都有“步”的“涉”字,趾形也寫得比較象形📁,見《合》20464.从“水”从“步”的“涉”可能是由它簡化而成的♜。《合》“1051正”有![]() 字🥷🏻,一般釋爲“涉”,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63頁“涉”字條所引“乙2317”即此例。但從文例看,此字似爲地名,而且此字所从二趾方向一致,一般“涉”字所从二趾形則分別象左右腳,即“止”和“
字🥷🏻,一般釋爲“涉”,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63頁“涉”字條所引“乙2317”即此例。但從文例看,此字似爲地名,而且此字所从二趾方向一致,一般“涉”字所从二趾形則分別象左右腳,即“止”和“![]() ”,彼此方向相反🚣🏽♂️🌦。所以此字似非“涉”字)。
”,彼此方向相反🚣🏽♂️🌦。所以此字似非“涉”字)。
再舉一個“昃”字的例子。“昃”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屢見⬆️,其字形通常用“日”旁和象人形的“大”旁的相對的位置關係,來表示日已西斜的意思🤸🏿♀️,是一個表意字(參看《甲骨文編》284~285頁“昃”字條)🗺🙌。戰國時代六國璽印的“昃”字仍然从“日”从“大”🍢,跟甲骨文相近(參看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166頁“昃”字條,文物出版社👩🏼🔧,1981)。“昃”有一個从“日”“夨”聲的異體“![]() ”,一般認爲最早見於東周時代的滕侯昃戈(參看高明《古文字類編》491頁“昃”字條)👩🚒。其實在武丁卜辭裏🌯,這種“昃”字也已經出現。有一條武丁時代的殘辭說:
”,一般認爲最早見於東周時代的滕侯昃戈(參看高明《古文字類編》491頁“昃”字條)👩🚒。其實在武丁卜辭裏🌯,這種“昃”字也已經出現。有一條武丁時代的殘辭說:
![]()
![]() 日大啓。昃亦雨自北,
日大啓。昃亦雨自北,![]() 昃啓。
昃啓。
《合》20957🤏🏻,即《殷虛文字乙編》32🫵🏼,後者較清晰🎂。
此辭的第二個“昃”字作![]() ,是表意字;第一個“昃”字作
,是表意字;第一個“昃”字作![]() ,則是从“日”“夨”聲的形聲字(即《甲骨文編》284頁“昃”字條所引“乙32”一例)。
,則是从“日”“夨”聲的形聲字(即《甲骨文編》284頁“昃”字條所引“乙32”一例)。
我們很難肯定,後來的“涉”字和“![]() ”字跟殷墟早期甲骨卜辭中的這種“涉”字和“
”字跟殷墟早期甲骨卜辭中的這種“涉”字和“![]() ”字之間,是否確有傳承關係♾。由於缺乏中間環節🛜,二者是不同時代的人所分頭造出來的可能性,還無法排除。不管事實如何,在武丁卜辭中就已經出現了从“步”的“涉”字和“
”字之間,是否確有傳承關係♾。由於缺乏中間環節🛜,二者是不同時代的人所分頭造出來的可能性,還無法排除。不管事實如何,在武丁卜辭中就已經出現了从“步”的“涉”字和“![]() ”字的現象,都可以看作漢字發展史上超前發展的例子👮。
”字的現象,都可以看作漢字發展史上超前發展的例子👮。
殷墟甲骨文有二百多年的歷史,由早期到晚期有不少發展變化。一般說🧞🫅🏽,比較原始的文字現象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減少的🛎。例如我們前面所討論到的反映甲骨文原始性的那些“逐”字異體🙋🏼,就都見於武丁時代和武丁至祖庚時代的卜辭🧜🏼🏊🏿♀️,而不見於中期和晚期的卜辭。又如“月”和“夕”的字形不分的現象,在早期和中期卜辭中時常能看到,在晚期卜辭中就已經極爲少見了。關於“月”“夕”字形問題,還有一點需要在這裏說明一下。武丁時代的賓組卜辭和緊接着的祖庚祖甲時代的出祖卜辭——它們跟同時代的其他組卜辭相比🗻,在字形上具有明顯的規範化傾向——對“月”和“夕”的字形已經作了區分。不過它們以“![]() ”爲“月”,以“
”爲“月”,以“![]() ”爲“夕”👨🦳,“月”比“夕”多一筆,跟後世正好相反💕。晚期卜辭才確定用多一筆的爲“月”🦧,少一筆的爲“夕”,爲後世所承襲。由早期到晚期,反映甲骨文超前發展一面的特殊字形,似乎也在不斷減少。例如前面舉過的“
”爲“夕”👨🦳,“月”比“夕”多一筆,跟後世正好相反💕。晚期卜辭才確定用多一筆的爲“月”🦧,少一筆的爲“夕”,爲後世所承襲。由早期到晚期,反映甲骨文超前發展一面的特殊字形,似乎也在不斷減少。例如前面舉過的“![]() ”見於早期👷🏼♀️、中期而不見於晚期🦗🆚,“涉”、“
”見於早期👷🏼♀️、中期而不見於晚期🦗🆚,“涉”、“![]() ”、“
”、“![]() ”則只見於早期。這跟反映甲骨文原始性一面的特殊字形的不斷減少,都是文字寫法的隨意性愈來愈受到限制的表現。總之🪚,由早期到晚期💇🏻🍩,殷墟甲骨文的文字面貌的複雜性有了明顯的降低。
”則只見於早期。這跟反映甲骨文原始性一面的特殊字形的不斷減少,都是文字寫法的隨意性愈來愈受到限制的表現。總之🪚,由早期到晚期💇🏻🍩,殷墟甲骨文的文字面貌的複雜性有了明顯的降低。
原文載韓國淑明女子大學校創學九十周年紀念國際甲骨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6年
校記🧒🏻🌯:
1第一段“《古文字學論集·第一輯·甲骨學特輯》”原手稿作“集”
2文中兩處引到《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均誤作“《古代文史研究初探》”
3文中引到《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原稿出版日期作“1949”
4《合》20715號卜骨,左圖為原書拓片,右圖為裘先生手摹
5“![]() ”字見於辭尾記“十月在
”字見於辭尾記“十月在![]() ”的一條殘辭🤙🏿。在同時期的卜辭中😦,還有幾條也在辭末記“十月在
”的一條殘辭🤙🏿。在同時期的卜辭中😦,還有幾條也在辭末記“十月在![]() ”。此句“尾”字和“末”字上有記號🏑。
”。此句“尾”字和“末”字上有記號🏑。
蔣文校錄
-

shibuwodai 在 2008/1/28 20:48:35 评价道:第1楼
一点点提示:本文最后一段中有这么一句话🧘🏻♂️☄️:“不過它們以‘
 ’爲‘月’,以‘
’爲‘月’,以‘ ’爲‘夕’💝,‘月’比‘夕’多一筆,跟後世正好相反”,其中“‘月’比‘夕’多一筆”🫲,似乎应为“‘夕’比‘月’多一筆”👩🎨。
’爲‘夕’💝,‘月’比‘夕’多一筆,跟後世正好相反”,其中“‘月’比‘夕’多一筆”🫲,似乎应为“‘夕’比‘月’多一筆”👩🎨。 -

子居 在 2008/1/28 22:27:01 评价道:第2楼
果然只是一点点,提示了也还是没懂。

-

shibuwodai 在 2008/1/29 19:49:22 评价道:第3楼
一点点看法:本文中裘先生在括号中以按语的形式写了这样一段话:(武丁卜辭中還有在“水”的兩邊都有“步”的“涉”字🧶,趾形也寫得比較象形,見《合》20464.从“水”从“步”的“涉”可能是由它簡化而成的。《合》“1051正”有
 字,一般釋爲“涉”🪙,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63頁“涉”字條所引“乙2317”即此例。但從文例看😧,此字似爲地名,而且此字所从二趾方向一致🤦🏿♀️,一般“涉”字所从二趾形則分別象左右腳🦸🏽♀️,即“止”和“
字,一般釋爲“涉”🪙,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63頁“涉”字條所引“乙2317”即此例。但從文例看😧,此字似爲地名,而且此字所从二趾方向一致🤦🏿♀️,一般“涉”字所从二趾形則分別象左右腳🦸🏽♀️,即“止”和“ ”,彼此方向相反↙️。所以此字似非“涉”字)。《甲骨文合集》第六册19286号甲骨中有一个字🤴🏽,也是“涉”字🦥🌯,但此涉字不同于《合》20464中的涉字✊,此涉字“水”的左边所从二趾方向不一致,呈步字形👨🏿🚀,右边所从二趾方向一致。颇疑裘先生所举的《合》“1051正”中的
”,彼此方向相反↙️。所以此字似非“涉”字)。《甲骨文合集》第六册19286号甲骨中有一个字🤴🏽,也是“涉”字🦥🌯,但此涉字不同于《合》20464中的涉字✊,此涉字“水”的左边所从二趾方向不一致,呈步字形👨🏿🚀,右边所从二趾方向一致。颇疑裘先生所举的《合》“1051正”中的 字,是由《合》19286中的涉字简省而来,情况正与裘先生所举的,由《合》20464中的繁体涉字简化为从“水”从“步”的“涉”字相同。
字,是由《合》19286中的涉字简省而来,情况正与裘先生所举的,由《合》20464中的繁体涉字简化为从“水”从“步”的“涉”字相同。 -

llaogui 在 2008/1/31 16:06:56 评价道:第4楼
補個原刊封面。裘先生文的韓文本在1-6頁👩❤️💋👨🔱;中文本在143-146頁。

-

海天 在 2010/3/5 15:51:32 评价道🫶🏻:第11楼
只有《合》10945“貞:弗其擒🆕。十月。在
 ”一條是完整的。
”一條是完整的。是10995🟪。
Copyright 富达平台 - 注册即送,豪礼相随!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84952号 地址:富达注册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200433
感谢上海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總訪問量:706350
 0060從文字學角度看殷墟甲骨文的複雜性
0060從文字學角度看殷墟甲骨文的複雜性